对神经症的判定,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
文章转自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社会心理学、女性心理学的先驱。《我们内心的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是霍妮晚期的成熟之作,这篇笔记主要基于我在阅读该著作过程中获得的体会与启发,同时也参考了她早期的作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与《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 1885-1952)
霍妮的精神分析之路,是从接受分析开始的。学医期间(1906-1013),霍妮经历了结婚、生子、双亲离世,不堪重负的她寻求精神分析的帮助,而她的第一位分析师正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后者也成为她的入门导师。
及至1920年,霍妮已是柏林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与亚伯拉罕一道创办了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并在其中执教。
作为一名女性精神分析师,霍妮在学习并教授正统弗洛伊德理论的同时,也带入了自己的思考。她对弗式(即弗洛伊德)“阴茎嫉妒”(penis envy)理论的批判,便是她日后开创女性心理学的开端。
1932年,为了躲避纳粹党人的迫害,霍妮移居美国,随着对沙利文、阿德勒、弗洛姆等人观点的了解,她的理论思想与分析实践中也越发重视文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而霍妮对弗洛伊德原教旨主义的“背叛”,也是其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所开创之精神分析的起点。

图:弗洛伊德;霍妮
随着她对弗式理论的修正与批判逐渐明晰,也因此与正统流派渐行渐远,直至1941年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她的执业资格。作为回应,她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以继续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
其后,霍妮相继出版了《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等作品。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与思考的日趋成熟与精细,霍妮对神经症的理解更完备、更系统。《我们内心的冲突》是进入霍妮理论建构的恰切起点。
对弗洛伊德的继承:批判与发展
对一位大师及其理论的继承,并非只能一成不变、亦步亦趋。虽然霍妮遭到自诩正统的精神分析流派的放逐,但这显然是一个“白马非马”的问题。“(我的理论)究竟是否称得上是精神分析?”
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以下简称《时代》)一书的序言中,这般自问自答:
“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路,目的在于考察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无意识过程获得表现的方式,并以心理治疗的形式使这些潜在的过程意识化,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就算得上精神分析。”
我同意她的观点。“精神分析”正如忒修斯之船,定义其存有及实在的是其破浪的历史及航行的方向,哪怕每一块木板都被更换了一遍,它依然是它。

在霍妮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弗洛伊德成就的认可,以及对原教旨主义可能窒息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忧虑。
在弗洛伊德所处的19世纪中叶,科学主义大行其道,学者们普遍相信理性终将胜利。摆脱了宗教钳制的自然科学如是;以人和人群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奉为圭臬。提倡研究社会事实的涂尔干、开创实验心理学的冯特,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冯特 涂尔干
人能超越时代,但无法抽离于时代,任何伟大的智识成就都诞生于前人智慧的结晶。被霍妮认为超越了时代思想的弗洛伊德,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他希望找到人类心理的普遍解释,正如物理学和化学那般。
人与人千差万别,但人之所以是人,最坚实的共性无疑是生物的、遗传的(无论什么种族、民族、文化背景的人,都有性交并生育的能力);所以弗洛伊德倾向于以人类共有的基础——生物性驱力——来解读无意识的结构与规律,以此找到对神经症与人类心理普遍的解释。
霍妮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正是始于对其泛性论、生物决定论的批判。事实上,弗洛伊德同时也看重个体生活环境,尤其是童年经历的决定性影响。
但霍妮认为,要发展精神分析理论,就必须修正他对“精神特性的生物性起源的过分强调”,并且重新关注被他所忽视的“文化因素”。

我认为,这里体现的,正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永恒诘问。一端认为人的先天因素(如基因、生物性、先赋地位)决定了一切的行为和发展,另一端则仅仅关注人的后天因素(如努力、社会性、成就地位)。
而事实是,两个极端都不可靠。
我们都处在先天与后天纷繁复杂的交互与动力之中,而我们的意志与选择,更令人生充满了偶然与多变。
沙利文、阿德勒、弗洛姆以及霍妮等学者对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平衡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偏颇。又如约瑟夫·安德森提出的“文化无意识”也填充了荣格“集体无意识”概念与个体之间的断层。
但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拿捏其中的尺度以避免任何一端的偏废。

文化因素构成了神经症的基础
霍妮是在两个维度上将文化因素纳入了精神分析视野的。
第一,是神经症的判定。接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霍妮(2016)认为,“神经症这种说法,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在使用中却不可能不具备其文化内涵”。因为,正常与不正常的界定是社会性的。
换言之,一个文化认为正常的心态和行为,有可能在另一个文化就被视为不正常;比如,中美对宠溺孩子的态度截然相反。
不仅不同文化的定义不同,同一个文化内的价值判断也会因时代而变迁;比如清代妇女被要求裹小脚、不能上学,而现代中国女性已占据职场的半壁江山。
哪怕是被视作神经症的强迫性特征,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被视作正常。比如,在工作、赚钱、获取权力上展现出来的明显的强迫性,会被秉持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主流社会认为是合理的;而那些阻碍了个人效率的强迫性行为,则被认定为是神经症。
归根结底,个体行为与心智正常与否的判准是由集体定义并强加给个体的,无论这个集体是由时间还是空间划分。

第二,文化因素构成了神经症的基础。这是因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深受文化的影响,从中习得价值观,并获得某种意义的来源。
若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本身带有冲突性,那么这种冲突性就以个人为载体再生产了出来,继而导致了人内心的焦虑,焦虑激发了防御机制,进而展现出神经症的症状。
以她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为背景,霍妮强调了三种文化的主要矛盾:个人主义式的竞争与基督教崇尚的仁爱;不断被激发的享受需求与需求难以实现的现实;个人自有的许诺与实际受到的局限。
这也是1976年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从美国经验出发所识别出的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
当然,文化千差万别,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矛盾及其特定的表现形式,这正是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必须要本土化的原由。
对每个文化内特定矛盾的识别,可以通过对来访者进行分析所得的经验素材,进行自下而上的归纳总结,当然也可以直接观察社会文化逻辑进行整体性的判断。正如霍妮所说,需要交替地使用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项工具。
哪些人更容易陷入神经症的泥沼?
既然文化无差别地对人们产生影响,那么,为什么只有部分人才会陷入神经症的泥沼呢?
霍妮对此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向:
一、有些人遭逢的压力更甚;
二、有些人对压力的反应更大(也即化解压力的能力更差)。

第一个问题并无法也不需要解释,显然这和个体独特的境遇有关,比如弗洛伊德无比关注的童年经历,也是因人而异的。第二个问题才是关键:难道有些人天生就更易敏、更不抗压吗?
或许当代的心理学会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归因为个体的生理差异。但是,这里又遇到了先前提及的先天与后天的交互,也即,后天的经历也有着旗鼓相当的影响力。一个基因的乐天派也可能在遭逢难以承受的人生变故时,陷入巨大的幻灭。
在此处,霍妮延续了弗洛伊德的基本判断——童年经历的关键影响,并提出了“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概念。
所谓“基本焦虑”,是指若一个孩子的童年经历令其内心不断生出孤独感、绝望感,对这些环境因素采取的个人反应会凝固为一种性格态度。
一个随时处在基本焦虑中的人,也即一个焦虑值的基线较高的人,自然更容易被点燃。
但也正在此处,她和弗洛伊德的分歧暴露了出来。弗洛伊德将成人展现出来的神经症视作幼年焦虑(及抵抗)的再现,而霍妮将其视为只是一种土壤。
若来访者在分析师的指引下,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问题归咎到童年经历,这恰恰说明了他严重的外化倾向,借此阻碍自己触及问题的核心——此时此刻的内心冲突。
童年经历所造成的基本焦虑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条件,正如火药爆炸也需要导火线,真正诱发神经症的,是“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这是霍妮理论体系中另一个关键的概念。

我们所面临的基本冲突
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不同于弗洛伊德将生/死本能视作基本的冲突,霍妮将重心放置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区分了三种人格(这三种类型是简化的、韦伯式理想型的):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孤立型人格。
第一种人格表现为亲近他人,一味顺从他人,是因为对他人的认可和需要有着强迫性的渴求。
第二种人格表现为对抗他人,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权力、地位和支配有着强迫的渴求。
第三种人格表现为回避他人,甚至与自我相疏离。
值得注意的是,霍妮认为,对抗基本焦虑的四种方式是:爱、顺从、权力和退缩。而后三种方式被划入了可催生神经症的范畴。或许在她心目中,唯一剩下的、兴许是唯一正确的、好的解决焦虑的方式,便是爱。
那么,霍妮的情人弗洛姆所写的《爱的艺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

弗洛姆
我们如何应对内心的冲突?
不难发现,这些对他人的态度——亲近、对抗、回避,几乎是每个个体都会采纳的态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处在类似的冲突与矛盾之中。
可以认为,产生神经症的原因,是采取了不好的应对方式,即防御机制,但防御机制却并非一定是不好的。
霍妮认为,防御机制有着正面的作用,若对缓解焦虑、整合人格没有丝毫益处,患者又为何会采取这些防御机制呢?不过,这些防御机制也可能有着巨大的副作用,或因急功近利而无法持久,又或酿成了新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它们治标不治本。真正的本,在于内心的那些冲突。

防御机制是尝试解决(霍妮特别指出是solve而非resolve)冲突的努力,但并不成功。失败了的防御机制层层叠加,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保护性结构,却唯独无法真正解决冲突。
后果就是:恐惧,人格衰竭,绝望,甚至形成虐待狂趋势。

那么,既然正常与否的标准由社会而定,那么是不是说明神经症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呢?霍妮认为,它并非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些冲突以及尝试解决冲突的失败努力,会造成我们创造力的枯竭和精力的巨大损耗,令人无法集中精神追求自己的发展。
这种对人性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这是健康、良善、好的追求。
更进一步,由于神经症的根源在于内心冲突,而内心冲突需要社会文化(至少是部分地)负责,霍妮论证说:
“神经症说到底还是特定文明的产物,因此对人的毒害无疑是对那种文明制度的严厉控诉。”

基于此,她设下的分析师伦理也清晰可见:来访者是否需要接受分析应当取决于病人的态度是否损害了他自己的发展,是否损害了他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分析师不能以自己的教育、传统、信仰和道德为依据。
比如,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分析师依据宗教教义而尝试改变患者性滥交或自渎的行为,而并非因为这些行为阻碍了来访者的自我实现。
霍妮的局限,以及后人继续前进所仰仗的巨人的肩膀
不管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是对精神分析的发展,我认为霍妮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她触及了一个巨大的学术领域却远未成功解答,即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与互构。
社会(集体)到人(个体)与人到社会的过程,是同步发生的,是一体两面的,涉及了法律、道德、规范、话语、符号等诸多权力部署,此间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在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来回穿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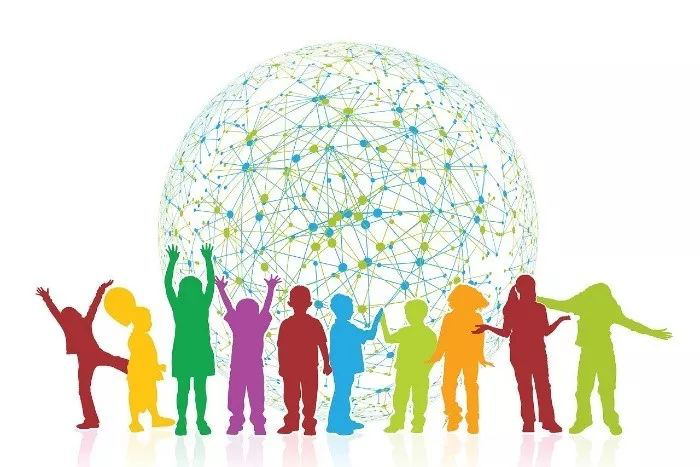
在这个意义上,霍妮确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也提供了精神分析在宏观维度应用的概念基础。
不过,当霍妮强调文化对个体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同时,却未讨论个体如何组成社会,以及如何推动其变革。
有一个一矢中的的批评是,当霍妮清晰地见到文化矛盾对个体的负面影响时,仅仅提出如何透过分析治疗帮助来访者重整旗鼓,却丝毫没有考虑如何借助集体行动消除文化内根深蒂固的矛盾。按霍妮自己的话说,这样的策略岂不也是治标不治本?
除了实践上的问题,更大的问号留在了如何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是如何对个体施加了如此大的影响?个体(无论是否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再生产着文化内的矛盾?


在文化对个体的压制中,个体必然是中介,也必然是目标,个体既是客体也是主体;也因此,在神经症的语境中,个体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矛盾的二重性?
反过来,社会仅仅是人群的集合,别无他物。社会、文化等集体性概念都是一种建构,其物质性来自于活生生的个体,而虚构性又来自抽象和概念化过程。每一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社会、文化的生产过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分析,都是一种重塑社会、改造社会的行动。



霍妮强调分析师在进行分析治疗时必须考虑到道德因素,不
能基于个人的宗教、文化、传统等价值观偏好对来访者进行分析。
但同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分析师也应该时时反省自己的分析实践可能造成的宏观后果。分析师的治疗工作不仅仅作用于来访者,也把来访者作为中介塑形着他人乃至社会——尤其是当霍妮把与他人的关系置于分析的核心地位。
这些是霍妮的局限,也是后人继续前进所仰仗的巨人的肩膀。
主要阅读书籍:
[1]《我们内心的冲突》(2015,南京:译林出版社,王作虹译)及其英文原版;
[2]《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2016,南京:译林出版社,冯川译);
[3]《精神分析的新方向》(2008,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张长英、赵立影译)。
本文是2019级【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两年课程】中的一次考核作业,作者对霍妮的观点进行了提炼与反思,从一个更广阔的的角度探讨“神经症”,探讨文化对个人的影响。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是如何对个体施加了如此大的影响?个体又如何再生产着文化内的矛盾?以及如何借助集体行动消除文化内根深蒂固的矛盾?
而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既受它的滋养,也受它的束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与“文化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有相通的地方。